通观现下的大陆与西方学界,边疆史都是颇为抢眼、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即以近年来的热门史学思潮为例,从“何为中国”到“从周边看中国”,再及强调跨地域互动的全球史,一波波学术热潮都在边疆史范畴留下余温,推动领域聚焦议题的持续更新。至于西方学界的情形,自不待言——一批清史学者对清代中国广袤边关地带的关注,引起了迁延日久的学术争鸣与碰撞。在这样的逻辑下,作为一个从立国之初便承受着巨大边防压力、最终亦因边关失守而走向衰亡的王朝,明代中国的边疆问题获得了学者的持久关注,也不是令人意外之事。本文择取笔者在2024年末或因工作缘故、或由兴趣使然而集中阅读的数部关乎明朝边疆史的学术作品,进行天马行空式的关联和碎碎念风格的点评,权且作为对近年来明代边疆史研究,尤其是海外学界相关学术演进情形的一次管窥。
窦德士著,陈佳臻译:《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天地出版社,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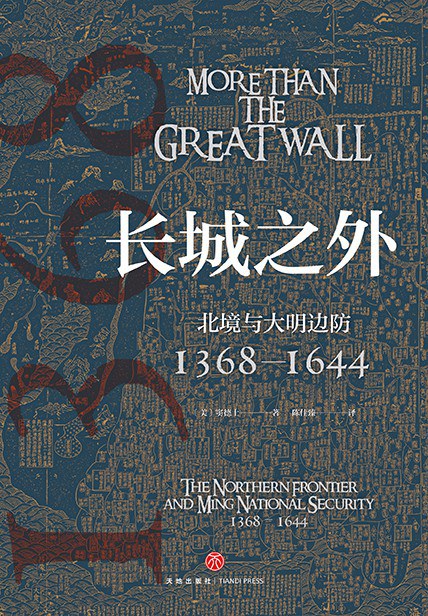
谈及明代的边疆与边防,恐怕大多数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明蒙对抗与明长城的修筑。诚然,不论是明初自洪永时代便开始酝酿、尔后在土木之变集中爆发的边防矛盾,还是明代中后期与“南倭”并行的“北虏”问题,甚至于最终压垮明朝的西北民变与满洲崛起,北境危机伴随有明一代始终。正因为此,明代北部边疆史吸引着无数学人的目光。但也恰恰是由于关涉史实的繁复驳杂、所涉史料的庞大体量,少有学者敢于在一部专著中处理整个断代的北境边防议题。在这个意义上,纵然本书作者对于史料的处理多少存在误读和简化,我们也应该对其以八十高龄挑战学术高山的勇气致以敬意。
《长城之外》的作者窦德士(John W. Dardess),生于1937年,于2020年去世,是美国老一辈明史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嘉靖帝的四季》《长城之外》等书的译介,窦德士之名逐步为大陆学界所知。被万明教授称作“美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的范德(Edward L. Farmer)与窦德士年龄相仿并仍健在,相比之下,窦德士或更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窦德士的学术关注与其职业履历一样丰富:他先后求学于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长时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在将学术目光投向明代北境边防之前,他亦曾关注过明初专制体制、明中期宫廷政治、明末党争、明代江西地方社会,以及元代后期的政治思想史,可谓涉猎广泛。而《长城之外》的英文原著More than the Great Wall: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Ming National Security, 1368-1644于2019年出版,是作者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笔者在此处并不打算系统介绍《长城之外》的学术旨趣、观点抑或得失,因为此项工作已在崔继来兄的详密书评中得到了很好的完成(《从细节深处透视大明边防——读〈长城之外〉》,《澎湃新闻》2024年5月21日)。质言之,本书循时间线索梳理了明朝历代对蒙活动大事记,并以边防政策为纲,将明代北境边防分为了以战争为主轴的洪武到宣德时期、以防御为特征的正统到隆庆前期,以及从和谈到崩解的隆庆中期以至明末。本书对非专业读者并不算友好,因为读者很容易被巨量的细节淹没,而这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在“序言”中,作者便直言明代可以在近三百年中相对成功地守御近三千公里长的北境防线,其答案“当然无法简单地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火器发展史或长城修建史中得到,而要从一连串经年累月的事件叙述中去总结,从一系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涉及为迟滞对中原永无止息的袭扰,消除事关存亡威胁的战事、谋略、决策、行动的史实中去发现”。以此,要想理解大明的边防演进,便只能将之全盘呈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叙述是一本完完全全的流水账。在铺陈史事的间隙中,总有作者精辟而谨慎的点评与概述。用心的读者,当不难在这些夹叙夹议中体味到作者的深厚功力。
在这里,笔者更希望将《长城之外》放在西方世界的长城研究脉络里进行讨论,以期检审英文学界近年来的学术范式转换。关于明清时代直至二十世纪初西人对长城的认知,赵现海已有专文讨论,兹不赘言(《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一项“长城文化史”的考察》,《暨南学报》2015年第12期)。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拉铁摩尔和威廉·盖洛为代表的探险家留下了众多关于长城的游记和影像材料,通过记录历史现场的方式为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而立体的长城形象。二十世纪后半期,近乎今日我们所熟知的科学意义上的长城研究数量日增。如林霨(Arthur Waldron)于1990年出版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便是新世代长城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林霨一方面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了明代长城的修筑过程,并将之与明代中期的“收套/弃套”战略结合而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则考察了作为文化符号的长城在近代中国被政治化的过程:长城与中华民族精神逐步绑定,且被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文化建构,直至最终形塑了层次多元的长城神话。林霨这部分的书写显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史风潮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品出了些许“历史三调”的味道。
林霨以后的西方学者多就长城的象征意义展开文化研究维度的讨论。如蓝诗玲(Julia Lovell)2006年出版的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 – 2000 AD 便对东西方之间围绕长城所代表的“伟大民族象征”与“文化孤立主义”之截然二分进行反思。蓝氏认为,长城两千年的庞杂历史已然确认了这座伟大建筑文化意义的灵活多变,它因之并非文明和野蛮的界限,而是对历史流动性和相对性的预示。与蓝氏观念异曲同工,201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鹏(Carlos Rojas)专著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同样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对长城的象征意义展开讨论。罗鹏尤其关注长城传说,认为隐含在这些传说中的“儒家思想的仪式和隐喻”是理解长城的重要思想基础。而别出心裁的是,罗鹏特别关注了一系列“长城文本”中蕴含的女性力量的流动,认为长城并不仅仅是父权家长制所蕴含的威权与武力的象征,诸如“宣太后和义渠王”“昭君出塞”和“孟姜女哭长城”等女性传说也指向了长城象征的灵动与脆弱,而恰恰也就是此种不确定性使得“长城”的象征意义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
循着这样一种学术脉络,可以认为窦德士的《长城之外》算是回到了林霨研究的实证主义发端。诚然,在窦氏1992年对林霨专著进行的书评中,他便已经盛赞林霨对明代长城历史的研究了——而在《长城之外》中,也几乎不见窦氏对长城文化符号意义的解读,这可以看作是老派学者对传统史学路径的回归。相较而言,年轻学人则在“全球史”的范式风潮下将长城研究带入了新境。如匹兹堡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鄂可森(Christopher Eirkson)便在其博士论文“Ideas of Empire in Early Ming China: The Legacy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Chinese Imperial Visions, 1368-1500”中将明代中国的“建墙”行为放置在广大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鄂可森认为“建墙”不仅仅是明代中国所独有的现象,而且在其时欧亚大陆各处广泛存在。如沙俄帝国便在不断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与草原游牧民族发生摩擦,因之开始建墙以应对具备高机动性的游牧者。在与草原世界互动的维度上,明代中国在诸多方面都与其他欧亚政权具备可比性。例如正统皇帝被游牧民族掳走并囚禁之事,其实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奥斯曼帝国同样发生过。1402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大军在战争中俘获并囚禁,此一史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政体在之后的发展方向。近日笔者在收听播客的时候,得知罗新教授亦将进行关乎长城的旅行写作,他不仅仅走访了明长城沿线的很多村寨,还对伊朗长城、不列颠半岛的哈德良长城等有身体力行的感受和体验。笔者以为,比较史学的框架或许可以成为深化理解明代中国北部边防与长城文化的可行路径。
David M. Robinson, 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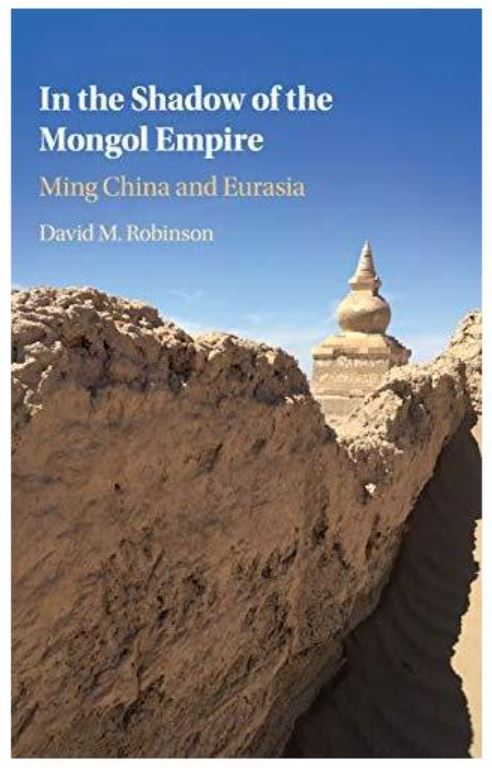
与《长城之外》的关注点相似,美国柯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亚洲研究暨历史学讲席教授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的近著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暂译名:《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明代中国与欧亚世界》,下文简称《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也处理了明朝与其草原强邻的关系,并将时间聚焦于洪武时代。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鲁大维之名当不陌生,其著作如《帝国的暮光》《神武军容耀天威》等近年来被批量译介,最新翻译出版的《称雄天下:早期明王朝与欧亚大陆盟友》亦颇受好评。事实上,《称雄天下》与《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本为姊妹篇,学术聚焦一以贯之,且以后者为上篇。又据卜正民(Timothy Brook)透露,在投稿给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两书甚至本为一更大部头的作品。惟出版社从篇幅、出版和市场角度考虑,要求作者将之拆分为两本。因此,若可将两书对读,便更容易把握作者近年来所谓“将明代前期历史放在元明易代的语境中深化理解”的倡导。
《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核心议题,是朱元璋如何在一个满溢着蒙古时代政治文化遗产的欧亚大陆强化自己的权威及宣称明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鲁大维认为,蒙古时代在欧亚大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留下烙印,存在感与显示度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这个逻辑下,蒙古时代的影响力有多大,朱元璋的压力就有多大。作为一个非黄金家族成员、没有娶到黄金家族女子、没有在元朝行政体系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的小人物,朱元璋如何向全世界证明他自己,这是鲁大维想通过此书回答的问题。
笔者关于此书的详尽书评将在一份专业期刊发表,此处仅做节略式的概括并谈一谈大体感想。《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二、第三个部分是此书的核心章节。在这两部分中,鲁大维分别讨论了朱元璋向国内臣民及欧亚大陆其他政权表达他理解元明鼎革的方式,并通过种种策略的文本叙述来达到他强调自身合法性的目的。为了概括明廷对蒙元时代的叙述策略,鲁大维提出了“成吉思家系叙事”(Chinggisid narrative)的概念,并以“叙事”一词所蕴含的“具有目的性的观点叙说”之意来提炼明初朝廷对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乃至整个蒙古帝国与时代的评述策略。在鲁大维看来,朱元璋时代的“成吉思家系叙事”绝非很多人认为的平面的、程式化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值得细细拆解的、能够反映洪武朝政治文化的文本凝聚。如情感态度激烈的“反蒙古”言论,显然是将国内臣民视作主要听众。而大元国运已失、明代元兴实属水到渠成的自然之选这样的叙事,则主要是说给北元朝廷、尤其是身处明初疆域东南西北边地的那些摇摆者听的。与军事行动相比,这样的“宣传战”对于明朝开疆拓土、稳定边防而言同样重要。
如果说该书的第二部分主要呈现的是明初“成吉思家系叙事”的国内版本,那么第三部分则凸显的是此一政治文化的外向输出。例如《给大汗的信》这一章便考察了朱元璋在二十余年间向妥欢帖睦尔、爱猷识里达腊、脱古思帖木儿所发出的十余封信件。在这些信中,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为何元运已失、为何他能够代元而立,以及为何这几位大汗应该接受甚至拥抱这样的变化。值得说明的是,鲁大维在这一部分中对大量敕谕进行了全文英译,为日后学者的翻译工作与中英对读提供了重要参考素材(窦德士专书亦对大量明实录节段进行了翻译,或可给需要英译相关文段的学者提供不少便利)。除此之外,鲁大维在分析具体文本内容时亦尤其注意明初朝廷对汉文与蒙古文、波斯文之间的翻译问题的处理。即便从文本的角度出发,亦可推见明廷和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诸多政权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的结论部分对全书中的很多观察进行了系统化的概述和提炼。鲁大维认为,朱元璋之所以面对各类听众不厌其烦地叙说蒙古帝国的崛起、荣耀与衰微,是因为这样的表述拥有广大的应用场域:明初的“成吉思家系叙事”不仅可以合法化朝廷对于权力的掌握、提醒人们元朝兴复的无望,还对那些尚持观望态度的豪强输出着“附明即得生、附元即灭亡”的道理。蒙古时代是欧亚大陆诸多政权的“起点”,所以“成吉思家系叙事”是一种切合跨地域语境的、大家都能听懂的政治宣传。而这种叙述的底色则是“规劝”。在鲁大维看来,既有研究对于朱元璋与洪武朝的专制主义特质瞩目甚多,往往将其理解为杀伐决断的绝对权威,这当然是其尤为鲜明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论者可能较少看到他反复调整语汇、用一种规劝式的口吻进行政治表达的面向。在这个维度下,朱元璋的“成吉思家系叙事”展示出的更多是耐心、容忍与坚持,并且贯穿了洪武朝始终——这直接指向了朱元璋颇为看重却无可奈何的一个要素,亦即在十四世纪几乎可以被视作全球的欧亚大陆,对于如何处理蒙元帝国的政治文化遗产,是不分种族、宗教、文化的各地统治者共同思考的难题。《在蒙古帝国的阴影下》聚焦于元末明初的数十年,切面不可谓大,然关怀亦不可谓小。
卜正民为鲁大维这本书的姐妹篇撰写了书评,并发表于业内顶尖刊物《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这篇书评中他对鲁大维之研究不吝赞美之辞,认为这两本书是“很多年未有的关乎中国王权统治的最有分量的研究”。卜正民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代明史学者仍致力于观察明朝与世界的联系,尤其是借由晚明中国考察白银全球化将世界各地勾连在一起的形式。而新一代的明史学者则受到近年来学术范式的促动,更倾向于将元以降的中国放置在欧亚大陆的时空框架下进行考察。毫无疑问,鲁大维的一系列研究便是此一思潮转换的标志性成果。以此,我们不妨进而思考:如果明朝的前一百五十年尚在因应蒙古时代的影响,而后一个半世纪则与海洋世界发生了愈深愈广的联系,那么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理解这样的转变,又可以如何刺激我们去反思明代中国,反思这个朝代在元朝与清朝之间的位置,以及更广泛时空中的角色呢?
Sixiang Wang, Boundless Winds of Empire: Rhetoric and Ritual in Early Chosŏn Diplomacy with Mi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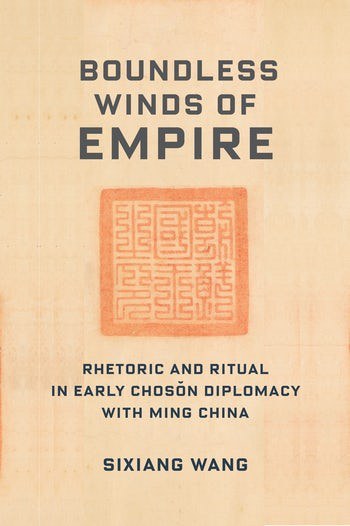
十余年前,葛兆光先生发出“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倡议,认为研究中国历史需要多几面镜子,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以西方作为参照,却忽略了朝鲜、越南、日本这些从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周边”的镜鉴作用。约略于同时,张伯伟先生站在文学领域的立场上亦强调需要加强对域外汉籍的重视。一时之间,文史领域双双开始对传统意义上东亚世界的“中心”与“外缘”角色进行反思,对学者的研究多有刺激。
王思翔的近著Boundless Winds of Empire: Rhetoric and Ritual in Early Chosŏn Diplomacy with Ming China(作者本人建议译名:《皇风无垠:明鲜外交中的修辞与礼仪》)或许可以放在这个脉络下进行理解——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王思翔本人的观点受到了大陆学界的启发,中英文学界的问题意识本就不同,呈现出相似的关怀,或许更多是“形似神异”的巧合。但双方共同展现的,则是对既有范式下对东亚世界区域格局僵化处理的不满,以及对跨地域联系、互动及相互影响的强调。
《皇风无垠》的作者王思翔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与文化学系副教授。在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前,其人先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又次第于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后职位。而拜宾大学缘所赐,笔者也算是忝入王思翔的同学行列。如果笔者的记忆没有产生偏差的话,王思翔的父母都是安徽人,因此其自小便是汉语、英语的双母语使用者,这从《皇风无垠》对大量诗词的精彩翻译、深入诠析中便可窥见一斑——有过相关文本处理经验的朋友都知道,翻译诗歌的门道有多深。而作者因为研究的关系,韩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亦俱佳,因之能够对跨区域历史研究驾轻就熟。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皇风无垠》聚焦的是“修辞与礼仪”在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与明帝国(1368-1644年)长达两个半世纪复杂互动中扮演的角色,亦即文字与书写是如何在东亚外交中发挥作用的。通过灵活的修辞策略,朝鲜一方面在“事大”的逻辑下保持对明忠诚,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对自主权益的强调。全书第一部分(1-2章)介绍了朝鲜与明朝沟通之初利用各种手段抹平双方之间张力的努力。十四世纪后期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千头万绪,半岛政权与蒙古势力藕断丝连,而李成桂取代高丽建国,在明朝方面看来亦有先斩后奏之嫌。因此朝鲜需要利用诸种外交手段来重新获得明朝信任,从而稳定区域局势。全书第二、三部分(3-7章)是专著的核心内容,检审了朝鲜士人对包括儒家思想和文学创作等文化行为的调用,并考察此类行径帮助朝鲜在与明交互过程中寻得“臣服”与“独立”之间平衡的方式和逻辑。如朝鲜使节坚持将朝鲜,即“东国”,纳入古之圣贤所倡导之文明场域,这样便可以在树立朝鲜文化权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驱散明廷对朝鲜半岛投射的复辟主义阴影;而在对具体外交实践中的礼仪进行分析时,王思翔也力图呈现明鲜双方是如何就繁复礼仪的文化内涵进行协商甚或较劲的——在这个意义上,外交礼仪便不仅仅是符号化的形式主义,更是暗流涌动的权利博弈场域。甚或在军事协作的过程中,明、鲜军队之间的抵牾如何与政治文化场域中双方高下分明的阶序关系自洽,亦是此部分的关注主题。而在全书的第四部分(8-10章)中,王思翔则重点关注《皇华集》,通过分析朝鲜文士与明廷使臣的唱酬之作中展现出的修辞策略,作者论述了朝鲜朝廷和明朝统治者如何共同打造明朝的所谓“帝国意识形态”。以此,在东亚区域格局的逻辑里,明、鲜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便不仅仅是儒家思想所定义的政治原则的简单衍生,亦非明朝世界观的自然延伸,而是产生于朝鲜王朝与明帝国之间有关文化与政治传承的复杂互动。
《皇风无垠》在西方中国学的学术脉络中所处位置如何?笔者以为,是书应当放在关乎“朝贡体系”讨论的延长线上进行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费正清学派提出用“朝贡体系”的概念理解古代东亚区域秩序。此后的数十年中,历史学家对于此一框架多有批评,认为“朝贡体系”的叙述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以至于卫思韩(John Wills Jr)一度将“朝贡体系”比作一艘沉船,说它没有任何值得打捞的价值。而即便“朝贡体系”的相关讨论存在扁平化解读或文化沙文主义等多方面的偏颇,学界一时半会儿也寻不到合适的替代概念,以至于柯娇燕认为“朝贡体系”已然获得了永生。相较而言,在历史学家对朝贡体系大加批判之际,西方学界的政治学家们却对此框架欣赏有加,尤其认为朝贡体系提供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西方国际关系的东方世界对应物。众多政治学家在2015年的《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和2017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组织了两期特刊,后者的特刊主题甚至直接叫“朝贡体系万岁!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展望”(“Long Live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Future of Studying East Asian Foreign Relations”),可见相关讨论的热度。
近年来,关乎“朝贡体系”的讨论在历史学界似乎有回暖之势,但仍以批评为主。如卜正民领衔编辑的《天命:成吉思汗以来的亚洲国际关系》(Sacred Mandates: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Chinggis Khan)便提出藏传佛教在后蒙古时代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中亦发挥了重要的润滑剂角色,基于儒家伦理的朝贡体系并非统摄性的外交准则。如若聚焦到明代,虽然很多学者曾经将明代中国视作中国历朝历代中实践朝贡体系最完备彻底的王朝,但根据Felix Kuhn的最新研究,作为外交工具的朝贡体系仅仅是明廷维系与外界关系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手段中的一环而已(“Much more than Tribute: The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s of the Ming Empire”)。
近世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是近年来英文学界反思朝贡体系的典范场域。2018年,宋念申出版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讨论一直以来较为稳定的中朝边境是如何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被流民、战争、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要素扰动,而中朝图门江边界的划界,则指向了以朝贡体系为准则的传统东亚秩序最终的“现代转向”。同年,王元崇亦出版专著《重塑中国》(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聚焦清代的中朝关系。不满于既有研究中“朝贡体系”的解释力度,王元崇提倡以回归历史语境的“宗藩关系”概念讨论清代“中华帝国”所强调的区域秩序,并希冀以朝鲜为镜,考察清代中国如何形塑和表述自身的政体性质和与世界交往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皇风无垠》几乎可看作《重塑中国》所涉议题的“明代版本”——所不同者,在于王元崇通过关注清朝与朝鲜的互动来理解清代中国的帝国形塑,而王思翔则经由考察明朝与朝鲜的往来去检审朝鲜方面的政权建构理路。在他看来,僵硬的“朝贡关系”框架无法全面概括明朝与朝鲜的关系,朝鲜方面在双边关系中并不失语,而是在动态的外交实践中灵活调整自己的身段,通过遣词造句的外交辞令、文学创作及仪式展演尽力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不开罪天朝上国的华夏中心主义逻辑,另一方面也在此过程中完善了属于半岛的政权形态和处事逻辑。









 冀ICP备15028771号-1
冀ICP备15028771号-1